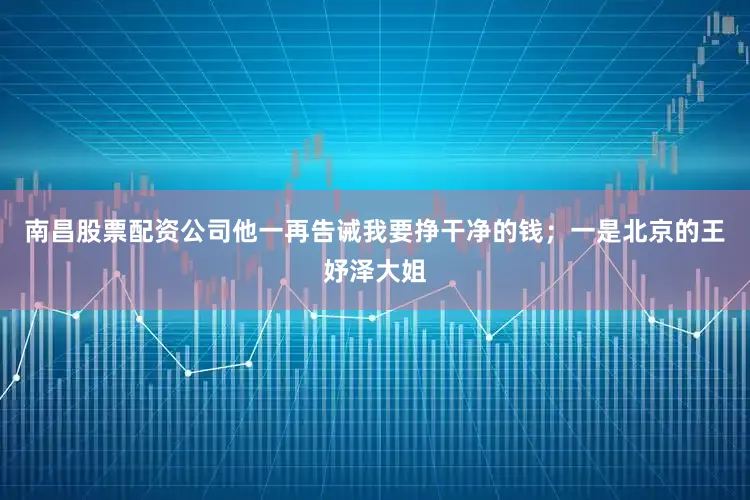
文︱孙玉良
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先生去世了,许多人都在悼念他。蔡澜以美食家、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世,其谈笑风生、潇洒不羁的形象深入人心。然而悼念他的文章中也有杂音,项立刚就爆料这位看似逍遥的文化名人,早年是靠拍三级片赚第一桶金的,不干净。在我的朋友圈中,有两位好友一直在提醒我。一是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李向安律师,他一再告诫我要挣干净的钱;一是北京的王妤泽大姐,她一再告诫我要“正心正念正行”,就像观音菩萨那样谆谆教诲。

人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?许多人的人生其实是蔡澜式的,为了第一桶金不择手段,先把钱赚了再说。我们看许多企业家,如果追根溯源,他们的第一桶金很少有干净的,或偷税漏税,或偷工减料,或掺杂使假,或出卖尊严,或吃软饭,或巴结人,或为了垄断市场拉帮结派加入涉黑组织,甚至为了金钱利益铤而走险,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所不惜。有人说“企业家多是有原罪的”,一点也不假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“投机倒把罪”、“抽逃注册资金罪”,到现在的“非法集资罪”、“集资诈骗罪”等等,屡见不鲜。蔡澜也不讳言他不光彩的经历,甚至坦言:\"年轻时觉得没什么,现在想来确实不太光彩”。
但显然人大多是有羞耻心的,所以我们观察到,许多人挣了不干净的第一桶金后,拼命洗白,淡化或掩藏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。有的成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,有的做慈善成为“公益大使”,有的出国后摇身一变成为“爱国华侨”,等等。“洗钱”甚至成为一种行当,想方设法要让挣来的不光彩的钱变的光明正大。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,人类历史成王败寇,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也同样如此。我们看许多“白手起家”的励志故事背后,实际上并非白手起家,而是另有隐情。这此自相矛盾的故事背后,隐藏着许多人对生存与理想的挣扎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?某个人之所以穷,是因为他挣的钱太干净了。

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,人要想在商业社会中立足,常常不得不向市场低头。金庸办《明报》初期,也不得不刊载些软性色情内容以维持销量;倪匡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写小说就是为了赚钱。这种\"先污染后治理\"被称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智慧,构成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灰色地带。蔡澜后来转型为美食家、作家,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自我救赎。他用余生对美食的纯粹追求,来洗涤早年的商业原罪。这种文化人格的分裂与整合,不只发生在蔡澜身上,许多人身上都有类似的影子。
李向安律师是我认识多年的好友,他对\"干净钱\"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。他曾说:\"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钱没有气味,但来路有”,这句话让我想起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在巴黎名利场中挣扎的年轻人,他们最初都怀揣理想,最终却被金钱异化。对金钱的力量,我们常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,既向往又心存恐惧。李律师的坚持提醒我,当第一桶金沾染了道德污点,后续的财富积累就会像滚雪球一样,将最初的污点无限放大。干净钱不仅是对外的道德要求,更是对内的心理保护——它让我们在夜深人静时,能够坦然面对镜中的自己。
王妤泽姐姐的\"正心正念正行\"则指向更高层次的生命境界。她常说:\"心不正,念必邪;念不正,行必偏。\"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心学智慧——\"心外无物,心外无事\"。在商业社会中,我们常常将成功简化为数字游戏,却忽略了心灵秩序的构建。当蔡澜晚年回顾自己的三级片经历时,那种隐约的愧疚感,或许正是心灵秩序被打破后的不适。妤姐的告诫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,而是提醒我们:每一个商业决策,都是对自我人格的塑造;每一分钱的来路,都在书写我们灵魂的模样。

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,\"挣干净钱\"与\"正心正念正行\"似乎成了不合时宜的老生常谈。当同龄人晒豪宅、晒名车时,坚守道德底线的我们显得如此笨拙而落伍。但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——明代商人沈万三富可敌国却最终家破人亡,而胡雪岩虽红顶商人却因贪腐身败名裂。这些前车之鉴告诉我们:不干净的钱财如同沙滩上的城堡,潮水一来便荡然无存;而建立在正念基础上的事业,才能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。
蔡澜的幸运在于,他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高的才华来完成自我救赎。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当我们站在金钱与道德的十字路口时,李律师和妤姐的告诫如同两盏明灯:一盏照亮脚下的路,确保每一步都踏在干净的土地上;一盏照亮远方的山,提醒我们不忘初心,方得始终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,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与金钱保持一种洁净的关系——既不做金钱的奴隶,也不做道德的伪君子。挣钱的过程,应该成为人格完善的过程;财富的积累,应该伴随心灵的成长。如此,当我们年老回顾一生时,才能坦然地对自己说一句:这辈子,我吃得开心,活得不亏心。
牛道配资,中国十大股票软件排名榜,股票配资8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